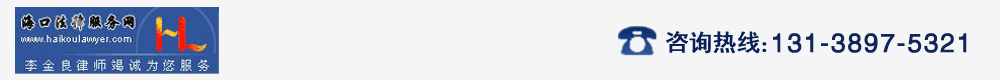因而,提供手淫服务是否是卖淫行为直接关系到大量的协助、组织提供手淫的行为是否是犯罪的问题,应属法律保留事项。如提供手淫服务是卖淫则很多行为即是犯罪,比如大量的发廊兼营为客人提供““打飞机””“吹箫”但不性交的情况可能构成容留卖淫罪。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修改法律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卖淫行为进行新的定义、做扩大解释之前,我们仍然应从立法者当时的实际意图及文意解释出发,认定“打飞机”不是卖淫,协助组织者不能入罪。即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赞同公安部的规定,也应出书面的文件加以明确,而法院则不能直接引用公安部的批复作为判案的依据。否则有违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看似有力的打击了犯罪,实则伤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我国的最根本的政治体制及各个机关分权制衡的初衷,最后导致民主不倡,法治无存。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本来公安部就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很多犯罪行为实际上是公安部在代替法院检察院的来审理,公安机关的预审基本上已在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理,不仅仅是调查取证的程序。一个公安部的批复若被看的如此重要,成为权威的法律解释,无疑更加加强了公安部的权威,削弱了其他真正的司法机关的权威,这对建立以法院为最高权威的法治国家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对于弱化侦查部门的权力,制约侦查机关的行为,保证基本人权、减少刑讯逼供也是非常不利的。
在文章行将结尾时,我又不得不说一点题外话,用刑法的手段来规制性行为,早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证明是无效的,简单的认为刑法可以压制不当性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重刑主义思想,是一种幼稚和无能的思维。中国的刑法中针对此类违法行为的犯罪打击不可谓不严,但是效果呢,不敢恭维,有人归咎于改革开放,归咎于国外有毒思想的侵染。实则不然,出卖性服务应该归咎于男尊女婢的男权思想,归咎于人类自身的缺陷,归咎于不合时宜的性观念。据考证,在原始社会甚至是动物世界中早已存在有偿性服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非正常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思想已经被清洗的如白纸一般,仍然没有消除不当性行为的存在。据我所知在文革时期,卖淫嫖娼仍没有被取缔,只是转入地下而已,如农村的暗娼等,在农村寡妇在邀请别人帮忙干农活之后以性服务作为交换等等,并不见得这些人都是衣食无着、非常的困苦百姓。经济问题在历史上若是一个重要的卖淫存在的原因的话,在当今社会这个原因恐怕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人民可以自由的进行性行为时(当然,这种自由是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规制的自由,但是这种道德和法律不是现在的打击压制不当性行为的道德和法律。)
要改变出卖性服务的现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那些指望通过刑法来控制有偿性服务的观点是不堪一击的,有偿性行为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一个人性的异化问题。生活在泸沽湖边的摩梭人几乎没有有偿性服务,因为在那里性资源是开放的,性资源的分配是有序的,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性伙伴,获得性资源。人们根本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获得性满足,而是通过初级的自给自足的配对来实现性压抑的发泄和性愉悦的达成。大家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即可发生性行为,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对价,也不需要中间人的出现和性服务市场的交换,至多双方进行一定的人际交往活动就可以了,如相互参加一定的社交活动,进行一定的语言和感情的交流而已。当然相互之间也会馈赠一定的礼物之类的东西,但是这种礼物与提供性服务的对价完全是不一样的性质。在有偿性服务的情况下,表明此种资源存在着稀缺,若不存在稀缺,有偿性行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何打破这种稀缺,有待于人们性观念、家庭观念的革命,有偿性服务不过是性革命的前奏而已。当人们不再把性看做一种可以操控的资源时,当性不再成为升官发财的途径时,当性不再成为男人奴役女人的借口时,当性交仅仅是两人交流的手段而非目的时,有偿的性服务也就不存在了。在此种意义上,性的开放可以成为减少有偿性行为,治理与性有关的社会顽疾的有效手段。如我们通常认